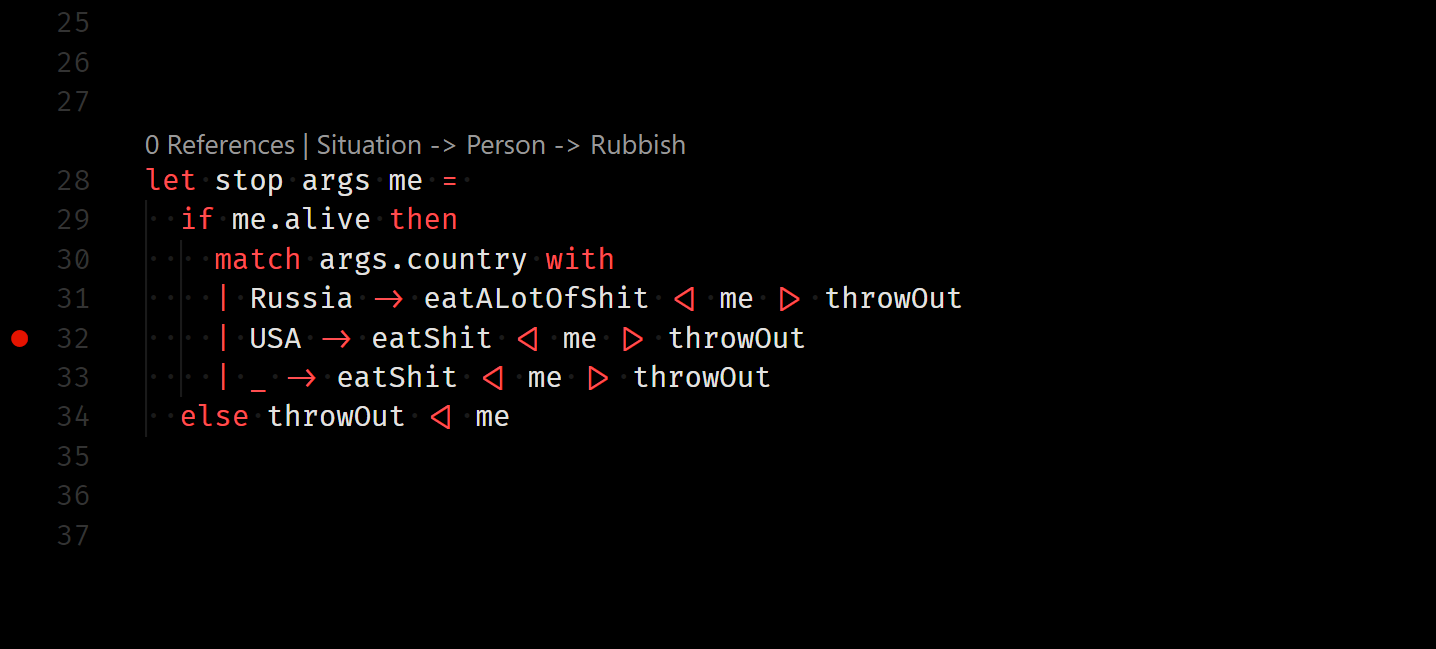
几年前,我在哈布雷杂志上读到阿列克谢·阿达莫夫斯基(Alexei Adamovsky)与Xored公司发生的丑闻。棘手的情况下,公司没有向这个人付钱,这个故事的主要敌人对我来说立即变得显而易见。另一件事是不可理解的。Adamovsky被雇用在该公司的新西伯利亚办事处工作,他确实想在布拉格办事处工作。为了同样的钱。我以某种方式说服了他们,然后去了那里。总的来说,他的权利,但还有其他事情,确实让我很受伤害-一个人真的讨厌住在俄罗斯联邦,以至于他准备以任何条件离开这里吗?
从那时起,我变得成熟并变得更加睿智-我开始理解渴望走得更远的愿望。当您从一出生就住在伊凡诺沃时,许多事情对您来说似乎很自然。贿赂dpsniks,恶劣的道路,在口袋里种了半克大麻的朋友。所有医生和老师的薪水微不足道,简直荒唐可笑,绝对没有改善的迹象,每步都警察,黑薪,而且每个人和各级人士都完全不遵守法律。
随着时间的流逝,拥有互联网的成年人已经开始发现信息-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任何传统的记者都能尽其所能地理解这一点-全世界任何人仍然不需要他们。但是优秀的开发人员可以随时随地移动,并且在那里生活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这种状况已促使人们搬迁。如今,开发人员搬迁已成为业界讨论中的重要部分。关于这一点的文章正在撰写中,围绕启动拖拉机的想法正在创建社区,来自搬迁公司的人力资源人员步履蹒跚地步入候选人市场。许多人认为,唯一合理的职业道路是离开这里,再也不会回来。
社区居高临下地嘲笑那些英语不好的失败者,我们所有人都假装原则上不阅读俄语文章。当您撰写有关Habr的出色文章时,人们会感到困惑-这怎么可能不是翻译!尝试告诉纽约的一些说俄语的同事,您可以搬到那里,但不想这么做,它会笑的。他不会嘲笑留在这里的愿望-他不会相信你,并且会嘲笑他认为是谎言的东西。
我为俄罗斯人感到羞耻。
俄罗斯工程师已经建立了许多非常酷的项目-一个JetBrains值得很多。我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但是我肯定知道我们知道如何变得很酷。我们在一些地方教他们编程非常好。当我看到ruvds的另一篇有关如何在js中呈现列表的翻译文章时,我完全感到震惊。是的,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前端开发人员,他们会写得更好,更深入-只是,我不知道,对他们有所帮助。
我与Microsoft顶级工程师在大型项目中并肩工作。我要说的是,他们在软技能,团队互动和业务实用性方面比我和我的俄罗斯同行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工程质量,那么我看不到任何相关性。我们有糟糕的工程师,他们也有。对我而言,代码质量的一般文化在这里甚至更高。
但是,我们的国家确实充满了坏事,有时候这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会帮助您闭上眼睛。当警察再次帮助赶出有条件的nzhinks时,宇航员在一次集会上又想起另一只轻骑兵,当您一年十次将悬挂装置固定在独轮车上时-出于自我控制和俄罗斯非常优秀的和谐理论,没有任何东西。
我去过几次国外,我真的很喜欢那里。但是即使经过三个星期的旅游,我也开始发疯。这些并不是很容易分解为逻辑论点的东西,我真的无法向自己解释什么是问题,但是生活在这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民,我的亲人,甚至是气候-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在西班牙沿镜面道路行驶时,我不想搬到西班牙-我希望我们拥有镜面道路。
当他们以我现在在俄罗斯的相同薪水将我搬到丹麦时,我有点不满。他们要么以为我很愚蠢,以至于我不了解生活价格的差异,要么他们以为我应该为“将肮脏的野蛮人运送到白人国家而舔他们的鞋子”。或者他们根本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没关系-我自己为他们考虑了所有事情。以最消极的方式,因为我不敢为自己在这里出生感到as愧,而且我不想假装自己讨厌这个地方。
这引起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想法。但是,如果不逃避问题而是设法减少问题呢?我确信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足够的人。我不反对-是的,最有可能是新西兰的州错了!=我们的州错了。
对每个人来说,好与坏的非二进制性质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直都忘记它。俄罗斯是一个坏国家,德国是一个坏国家。我的代码很糟糕,昨天刚读了他的第一本Javascript教程的人的代码也很糟糕。但是他的代码比我的代码差一百倍(我希望是)。而且“坏”一词的能力不足以描述事态。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代码不好,那将使我的所有经验以及我在该行业多年所做的所有工作贬值。不酷。
我来接受了。有些人不准备在此时此刻与邪恶作战,他们希望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国家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今天却没人在乎。在哪里,您的改善生活的倡议不会被警棍淹没,并且,您不会冒着风险坐在一条瓶子上发推文。谴责这样的人,或谴责那些在俄罗斯联邦中或多或少都正常的人,是一个坏主意,因为没有人有义务过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您将其视为东正教。那些对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想法感到沮丧的人,他们能够经历艰难的追求和行动-我的敬意。但是,人们,让我们做吧-尊重我不想要它的权利。
生活在这里并尝试-尽管没有成功-改善这里的一切-的想法具有生命权。我不会推销您可以那样做的想法,从天上拿起圣剑,然后将机器人砍成小人。但是仍然有可能。
有些人和组织每天都从事所谓的“反政权斗争”。他们的人不多,支持的选择也不是很广泛,他们的工作结果令人沮丧。好吧,他们把几个代表拖进了村委会,然后呢?我们希望,明天我们将在美丽的未来俄罗斯中醒来,罪恶感将被铲除,好人将开始民主统治这个国家。
但是我什至不知道该支持谁-因为没有人将文化和政治分开。我不能选择在文化上是保守的,而是拥有最自由的州,不会干扰您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政治运动-自由主义。至少如果我想生活得很好,他们不会告诉我如何友善。
但是,仅仅相信别人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总的来说,我不相信我会在这个国家看到更大的进步。我今年26岁,有两个孩子,我已经不再成长和发展了,我不相信我无聊的生活会永远改变。很有可能设置了向量,直到现在我死了,我将一直跟踪它,就像现在一样,无法分析我的动作,或者我意识中的任何破裂和发现,或者一般而言不重要的事情。
也许我会像今天一样在同一个俄罗斯去世,也许我会崩溃并在泰国倾倒,或者我坐下来向孙子孙女解释他们长大的好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的机会因此,因为我曾经决定这样做。
我有一个播客,这与habr结合在一起,是向他人传达困扰我的想法的唯一机会。我冒着巨大的声誉风险,邀请米哈伊尔·斯维托夫(Mikhail Svetov)参加有关发展的播客。然后,当他下定决心在哈伯峰上谈论它时,他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风险在于,开发人员通常是不政治的,此外,Svetova习惯于在自由聚会中讨厌,因为少数群体的权利不在他的议程中。结果,每个人都不高兴。
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我的声誉真的不值得该死。我来到这里,公开地写信,我不想在工作中工作,我对产品不屑一顾,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做不到。数十万人阅读了这些文章-我已经埋葬了我的职业生涯。然后,我收到了很多提议,并且理解了-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打喷嚏。
事实证明,开发过程中断,冒名顶替综合症,行业中丑陋的管理文化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无法承担风险并对此进行撰写。该国的情况比这重要一百倍。
我没有搬到丹麦,没有搬到泰,也没有搬到美国-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每一秒钟都会被我是白痴的想法所折磨。但是我仍然可以随时随地这样做,所以每天我都必须与诱惑作斗争。令我感到恼火的是,这种诱惑根本存在。令我感到恼火的是,与他的战斗似乎毫无意义-毕竟,即使我留下,我的女儿也会离开。
我希望留在家里的愿望是一种规范,而不是英雄主义。
观看我的播客